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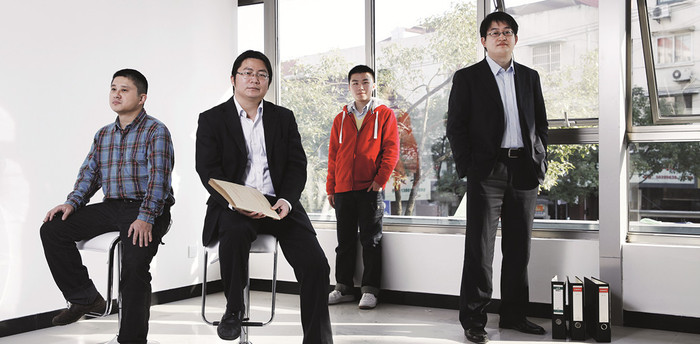
“北上广的公益组织最大的区别,拿最简单的捡垃圾为例:北京,捡垃圾是为了让政府也去捡;上海,捡垃圾为了组织一个社会化企业;广州,捡垃圾是为了推动公民社会。”主讲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资深NGO运营者曲栋的这个比喻像扔了一块石头,在台下听他演讲的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NGO从业者中溅起了水花。这是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服务中心组织的为期两天的法律培训,针对NGO从业者。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庄茂荣非常感兴趣,他是苏州人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秘书长,“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他追问道。在他看来,NGO是有钱人的游戏,“我们都是有钱人的职业经理人。”
NGO在中国是个复杂的、意味深长的词。它往往和公益、理想主义、弱势群体、争议、惨淡、资金短缺、信息不透明和混乱等词语纠缠在一起。
这是2012年11月23日,一个飘雨的深秋周末的清晨,很多人还在贪恋着被窝里的最后一丝温暖。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服务中心(Law Firm For NGO)组织的这场法律培训吸引了一群NGO参与者,他们自己也是NGO。
这是复恩筹备了一年、自2012年10月份注册成功以来的第一次活动。组织培训前,复恩像咨询公司做项目一样,针对22家NGO做了次法律需求调研。它们的培训内容建立在这次调研基础上,包括NGO最关心的劳动关系、对外合同法律实务和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两天,共四场。
这个结果带有明显的现实感——NGO虽然是公益性组织,但同样会遇到人事、薪资、对外签订合同等事宜,由于NGO的特殊性,在具体操作时和企业并不一样,同时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它们需要知道这些。
复恩取的是FOR NGO的意思。这是上海第一家为公益组织提供专业化法律支持服务的NGO。
NGO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通常被称为非政府组织。由于各国文化、法律等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叫法也不同。美国一般称之为“非营利组织”、“独立组织”或“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英国称之为“志愿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还有许多国家则用“社团”称之。
在中国,NGO又被叫做民间组织,分成“社会团体”(简称“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两类。社团的注册很困难,目前中国大多数NGO都是民非。
复恩可以说是第二代NGO,第一代NGO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第二代NGO的专业化、分工化程度更高,一个标志就是有专门为基层NGO提供服务的中间型NGO出现。
在曲栋看来,NGO正在成为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一种有益的补充。他觉得NGO和政府、企业最大的区别是:政府以执政为基础;企业以利益为基础;而NGO,强调的是以志愿精神为基础,自愿、非盈利、公益。NGO的资产是公共的,不属于任何个人。它的产权性质、资金性质、人事关系对应的是公共资产、信托资金、志愿关系。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现实中的NGO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困境,NGO人则是多元化的参与者。
庄茂荣更愿意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NGO,用做企业的方式来操作NGO的运营。对于“NGO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一说法,他解释说,“有钱人”是通俗意义上的说法,他们是出资者,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往往也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谁出资、谁买单,执行者就对谁负责,这是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则。
庄茂荣是苏州人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立者,苏州大学的MBA。对他而言,NGO是他为了照顾家庭退而求其次的最优选择。他的第二个孩子刚满月,他希望至少能照顾孩子们到幼儿园阶段,目前他离这个目标还有三年。他们夫妻原来都是公务员,忙起来孩子没人管。“NGO不用坐班,时间上很自由。”
庄茂荣把创办NGO看成是一场创业,之所以选择进入NGO而不是别的行业,“因为我以前在民政局,对这个行业最熟悉。以前慈善基金会五区七县的帮扶计划都是我一个人编制的。”人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购买它们的“社区矫正”服务。“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人本主要的工作是配合专门的国家机关,对置于社区内,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帮助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午休时,金笛来向庄茂荣讨教,在苏州新创一家NGO是否可行。金笛刚毕业不久,苏州本地人,是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苏州办公室的项目助理。这也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很喜欢NGO的工作,甚至萌生了要自己注册一家NGO的想法。
庄茂荣兜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你要想清楚,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理科的都知道数理推断,这到底是不是你的最优选择。把你最宝贵的一段时间扑在NGO上,值不值得?”
“我就怕他真的注册成功了,这个组织变成一个烂摊子,把自己陷进去,脱不开身。如果是做职员还可以抽身而退,创始人就没那么容易了。”庄茂荣解释说。
这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我现在就把自己陷进去了,走都走不掉。未来我还是要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做,三年后我还是要重返职场的。”
“我现在一分工资都不拿,拿多了不好看,人家会质疑你做NGO还拿那么多;太少了也不能体现我自己的价值,以后跟猎头谈薪水也不好谈。”
庄茂荣想力所能及做公益。“我特别认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倡导,在不影响自己家庭幸福的情况下做公益。”(注: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基本准则是“帮助愿意自助之人、慈善行为需要引入商业化管理思想、倡导非牺牲公益原则”)?
“我之所以没有给他鼓励,是希望他对自己、对NGO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社会组织分两类,一类是跟有钱人玩的,我觉得我目前都达不到这样的职业素养,另一类是跟政府玩的,这需要有资源。”
人本属于民非,现在已有40多名社工,还在继续招聘。因此,庄茂荣在听第二场关于“NGO组织的劳动关系”的法律培训时,非常认真。这也是在座很多NGO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尤其在加班、工伤和解除合同上,现场提出了不少问题,庄茂荣一边听一边飞快地记笔记。他这一年来到处参加培训充电,人本的财务和人事都是他一手在管,不学不行。
同桌的王耀南对这些却显得没什么兴趣,这个1984年出生的女孩看上去有些疲惫,即使在房间里还戴着一顶暗红格子的呢料八角帽,大半个脸掩在帽檐的阴影下。她是上海十二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公益项目总监,名片背面的绿底白字写了一堆自己在做的事,以及得到的媒体报道。
“我们在做生命故事剧场训练营与企业家精神剧场训练营,媒体报道有CCTV4流行无限栏目专题片,CCTV12见证栏目专题报道与中国首部公益微电影之爱的联想十二邻”。
她加入NGO的理由是为了理想,不过不是为了公益,而是可以实现她从事文化艺术类工作的理想。下午的讲座,王耀南没听完就中场离开了,剩下午餐后的一次性木质环保便当餐盒和几块橘子皮孤零零地躺在桌上。
王耀南已经几个月没收到工资了。用十二邻的创始人王俊晓的话说,“她是被我忽悠来的。”两人在一次讲座上认识,王耀南看到王俊晓特别活跃,四处和人搭话,于是也去聊了聊。听说王俊晓在做社区剧场,王耀南特别感兴趣,她一直想找一份和文化艺术相关的工作,但是苦于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之前她换过不少工作,制造业、酒店、金融等行业都做过,在辞职去十二邻之前,她的工作是做客服销售黄金。
“以前那些工作都特别无聊,跟个人兴趣一点关系也没有,做这个(十二邻)‘稍微’赚钱还能满足我的兴趣。”不过现在来看,“稍微”也没能实现。
“我一开始答应她的工资是5000元,后来也没兑现,现在每个月只有2000多元,还拖欠了好多个月了。”王俊晓挺无奈。
“你父母怎么看你这份工作?”
王耀南一开始没立即回答,王俊晓说:“你就直接说吧,我都知道,肯定是不满意的。”
王耀南说:“我要想想怎么说,怎么概括嘛。”
“其实很难跟我父母表述我的工作,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工作流程,父母的第一反应是‘这算什么工作?’”
“父母确实很难满意,最起码,正常缴纳社保应该是最低保障吧。”王俊晓补充说。
“那你们不交社保?”
王俊晓迟疑了一下,“交,不过交得很少,只有三四百元。”
在贾樟柯监制,王晶拍摄的公益微电影里,王俊晓穿着一件白T恤,走进小区里,听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再改写成剧本,由志愿者表演出来,和老人互动。十二邻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方式带动社区邻里互助,对于他人是一种人生体验、生命故事的分享,对于老人则是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释放。王耀南现在除了项目统筹、事务协调外,也会参与剧本的讨论与创作,这是她向往的文化类的工作。但是,机构运作艰难,王耀南也开始打退堂鼓。
“我打算再去找份别的工作了,这个可以兼职继续做志愿者。”王耀南说。
尽管现在十二邻只有王俊晓和王耀南2个全职人员,其余都是志愿者。但整个机构仍是得运行磕磕绊绊,非常拮据。事实上,缺行政管理经费,是所有NGO都在面临的问题。
NGO的整体薪酬水平处于社会平均收入的中下游水平,一般职员月薪两三千元左右,秘书长四五千元左右,NGO圈内做得最好的大佬们,月薪也不过在1万元出头。这造成了NGO在用工问题上的恶性循环。不能提供足够“体面”的薪资,留不住人才,没有人才,就更难和基金会对话,更难拿到项目。
复恩联合创始人奚志浩说,NGO全职人员的“空心化”非常严重。高管大多“不差钱”,至少不用为养家糊口发愁,底层人员虽然薪水较低,但进入门槛也不高。很多人抱着对公益的热情加入,又因为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失望而去。所以中间层非常缺乏,有能力的人往往最后都到企业里去,兼职做做公益。最后的结果是导致NGO工作效率低下。

奚志浩生于1970年,是一位投资专家,因为青海助学项目“高原绿洲”进入NGO圈。
NGO缺钱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NGO没有自身“造血”功能,主要资金来源于基金会的项目经费和政府的购买服务费用。而这些经费里,给予行政管理的费用比重非常低,基金会的一般观点认为,我的每一分钱都应该实实在在地用到资助对象上去,NGO的管理费用应该自己解决。而实际上,NGO虽然大多数依靠的是志愿者的奉献,但仍需要专职人员,比如财务、统筹等项目管理人员。
复恩2012年10月份对22家NGO的抽样调查(附表)显示,22家NGO中,全职人员3人以上的有20家,所占比例9成以上。3个职员的人力成本至少为10万元左右,对于一个项目往往只有几万元经费的NGO来说,是不小的负担。所以一些NGO的执行人只好虚报经费用途,拆补出人员经费。但是一旦被捐赠人发现,往往会丧失诚信,甚至导致捐助“断流”。
筹款是NGO的重要资金来源,但NGO创始人们对筹款是又爱又怕:靠筹款活着,又觉得活得憋屈,要被出资人牵着鼻子走。
最近王俊晓一直都提不起精神筹款。“很多基金会拿NGO当廉价劳动力使唤,一个项目没多少钱,要求又很高,需要很大的工作量,而基金会的资金又不包含或者只有很少的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
这个说法在复恩的筹款过程中也得到了印证,尽管10月份刚拿到注册证书,复恩的联合创始人之一陆璇已经筹得了两笔捐赠,一笔来自东方购物公益基金,总计1.7万元左右,也是这次免费法律培训的资金来源,这笔钱包含了8个半天的NGO专项法律培训费用,其中行政费用是1000元/月。
复恩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奚志浩主管财务,感叹说“这点钱给几位实习生发补贴还不够”。复恩现在一个全职的职员也没有,主要靠三位联合创始人和几位实习生做日常工作,其他活动依靠志愿者开展。实习生补贴是25元/次,有午餐补贴和公交补贴。复恩的活动筹备过程和日常运营中,实习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报酬实在不多。虽然培训已经做了,这笔1.7万元的“善款”却还没到账,好在注册时三人捐赠了10万元的注册资金,还能支持。
陆璇说这种贴钱做慈善的事儿并不少见。一些慈善基金会只为NGO提供所需资金的70%,剩下的30%要求NGO自筹。12月8日,在复旦举办的第一届上海市高校公益合作与发展论坛上,华侨基金会GO WEST项目在介绍经验时说,实践下来,第一年全额捐助的效果并不是最好的,反而是第二年70%的捐助效果最好。
陆璇听到这个说法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明知基金会的目的是挤行政管理费用的“水分”,但是“要想想全职的NGO人才拿多少工资,难道还要让他们贴钱做公益,让志愿者贴钱做公益吗?”
不过NGO也确实存在账目混乱的问题。十二邻的王俊晓说到机构开支时提到头一两年住几百元的房子,“从2010年开始,我们租的都是200多平方米的的大房子,以前是在闵行的一个别墅,现在是一个复式楼,2800元/月。”王俊晓和各地来的实习生都住在里面,最多的时候住七八个人,平时兼做办公和戏剧排练场地。现在王俊晓把其他房间都分租出去,只留一个大厅和一个房间,租金只要几百元。而且王俊晓喜欢买书,“我们最大的固定资产是书,而且很多都是艺术画册,或者港台版的影音书,每次去中国香港也会大量买书。这些书都很贵,现在有15个书架了吧。”王俊晓话里透着自豪。“这也很难说是固定资产还是个人的吧,”王耀南回应说,“不过以前就两个人在管理,都很粗线条的。”
公私不分、大手大脚、虚报账目,这是NGO的资金混乱里比较常见的问题。奚志浩也遇到过,参加法律咨询的律师拿出一张163元的当天出租车发票要求报销,碍于情面只好说下不为例。热爱家园的法律项目委员会改选,20余人租用了浦东的一个琴室开会,场地费用花了800元。
一些NGO在进行民主化的尝试,这也是人们愿意投入精力去加入、并且一起期待一个结果的原因,虽然现在还在拭目以待的过程里。
热爱家园前不久进行了一次民选。作为上海NGO的先行者,提起热爱家园,老资格的NGO人鲜有不知。它的前身是复旦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由曲栋、刘永龙、朱健刚于1996年10月创办。热爱家园历经10余年,在帮助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NGO专业人士,复恩的创始人陆璇是热爱家园的理事,奚志浩是监事,王俊晓也曾经是热爱家园的会员。
2012年3月召开的第十二届热爱家园会员大会,是刘永龙心口的一块伤疤。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下岗”了。刘永龙之前一直担任热爱家园的秘书长,同时也是法人代表,是热爱家园的创始人之一,公益圈里人称“老刘”。

刘永龙觉得,只要能够维持生存他就会继续做NGO。
2008年11月份,老刘辞去了上海印刷厂资产管理部经理的工作,成为热爱家园的秘书长。从月收入1万元的国企中层变为每月只有2000元的NGO人。钱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东西,他的底线是维持基本生活。他全职了3年零1个月,秘书长做了将近4年。有10个月左右他不领工资,义务干活。陆璇也说:“我会为了考虑热爱家园的问题睡不着,老刘会整宿整宿地失眠。”
理事会认可老刘的人品,但并不认可他的能力。曲栋一早就提议让刘永龙辞职,他觉得刘永龙的能力不够,限制了热爱家园的发展,陆璇和奚志浩与刘永龙谈过多次,希望他改进工作方法。“老刘人不错,但能力上有欠缺,而且他的个性比较强势,空间被他自己挤满了,别人就发挥不出来。”而且,更严峻的问题是筹款。这几年热爱家园的法律项目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逐渐式微的趋势。理事会认为秘书长筹款不力,没有很好地和资助人沟通,导致资助断流,秘书长应该负主要责任。
北师大法学院副教授刘培新调研了多家社会组织,研究考察民间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制度,他认为,热爱家园在筹款的潜在资源方面并不缺乏,但缺乏对项目成效的有效监控、跟踪对比,缺乏有执行力的项目成效结果。并且,由于项目人员的流失更替,没有很好地与资助方建立流畅的沟通渠道。
2012年会员大会上,全体会员表决未通过理事会的年终报告,监事会对报告直接提出质疑,表达对职员团队的不信任。理事会迫于监事会及会员大会的压力,只好请老刘请辞。“理事会要管好的就是秘书长,满足不了大家的期望值只能换人。”
陆璇还记得理事会做出决定的那天,老刘一个人站在最后面,面无表情,一句话也没有说。
老刘不再是秘书长之后,仍是热爱家园的法人代表,即便不再负责具体的管理实务,也要协助新任的助理秘书长顺利过渡。2012年10月27日,热爱家园法律项目委员会进行选举,会议依然是老刘主持。
陆璇和奚志浩作为理事和监事还在参与热爱家园的活动,不过,他们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到新成立的复恩上了。
复恩是陆璇、奚志浩和施君三人联合创办的。三个人都是热爱家园的资深会员,陆璇和施君是律师,主要参与法律项目比较多,陆璇同时还是理事。奚志浩主要参与的是“高原绿洲”青海助学项目,同时也是热爱家园的监事。创立复恩的想法萌芽于2011年11月29日,也是热爱家园的一次会后,三人在陆璇家里喝茶聊天,聊起理想中的NGO形式,决定要做一个专业的给NGO提供法律服务的平台,让更多的志愿者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发挥。当时陆璇刚参加完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公益律师培训”项目。“深受刺激,就想办一个专业的法律人的NGO。”
不过,就未来复恩的走向,三个联合创始人意见不一,或者说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方向。施君认为,只要有需求,无论有钱没钱都要提供帮助。奚志浩认为,免费项目可以做,但是一定要和未来的主营业务挂钩,可以说是埋下伏笔。未来的业务一定要向“金主”倾斜,解决资金来源,起码要有相应的资源来交换。陆璇觉得两个人的观点都有道理。至少现在,生存是第一要务。
非盈利组织不代表不能盈利,只是盈利不能用于分红而已。复恩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早日实现经济独立,不因为接受捐赠被牵着鼻子走,不因为那些琐碎的事情消耗人生,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可能也就是曲栋在开头所说的,上海的NGO最后喜欢搞成一个社会化企业的原因之一。
说到“NGO是有钱人的游戏”,陆璇和奚志浩都认可这个观点,陆璇说“有钱人就该玩这个游戏”。奚志浩进一步总结,“我们寻找合作对象和志愿者,也要找‘不差钱’的,至少不是靠志愿者补贴来谋生的,那些人不适合来做NGO。”
奚志浩说,自己兼职做公益的底线是时间,希望能够做一些有创意有价值的工作,不要在一些无聊琐碎的事情里消耗人生。“要不我还不如直接捐点钱给‘免费午餐’。”另一个底线是做公益不要让私人捐钱,做不长的,“这个机构应该有造血功能,否则就应该关门。”
奚志浩希望能够用平台优势弥补薪资的弱势。“我们要做的就是集合人力、财力,给志愿者提供更大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力量。”复恩的名片和宣传页都是大学生志愿者自己设计的,看起来有点粗糙,“一定要鼓励他们去创新。”
“没事,让他们放手去做。”
对于刘永龙来说,从事NGO的底线就是维持生存。12月13日早晨,他在一家茶餐厅等人。他刚从宁夏老家回来,辞去热爱家园的秘书长职务后,他在另一个NGO映绿兼职,筹备宁夏当地的NGO孵化项目。
他的生存状态已经逼近底线,但也不至于拮据。每月税后固定收入2560元,来自映绿的兼职收入,家庭开支以太太的四五千元工资支撑,有些积蓄,她想去办养老院。他们在上海有两套房,因为买得早,贷款都已还完。“尽管是老房子,但是万一有什么变故也可以卖掉一套应急。老家也有几套房,母亲和弟弟妹妹有所依持,尽到了对家庭的责任。”
“我们的生活都很简单,她也是热爱家园的志愿者,我们也是在热爱家园认识的。”
等人的间隙,他拿出一本已经翻得卷边的书念念有词地筹划着什么,书的封皮写着《罗伯特议事规则》,晚上他要去一个NGO机构培训,分享这个规则在NGO组织中的应用。
他认同德国人博盟的论文提到的NGO专业化陷阱,他更希望把它和公民社会联系起来。让他焦虑的是,专业化会导致精英路线,会走商业和服务路线。
他更赞同走基金会筹款的路,而不是自我造血。不怕监督,不急功近利,不怕麻烦。他希望人们想清楚自己做公益的本来目的。
外界对公益界的批评会让他有些激动。“一点公益都没做,就来批评我们做公益的人不干净。”“你批评要谨慎批评、合理批评。尽量用建设性的方法。”
“不是每个人的动机都经得起道德拷问,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裸露在别人面前。做公益不要问动机,而是看实际效果。”
显然,对他来说,结果更重要